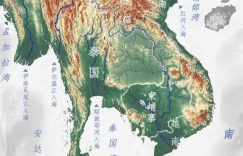“我”是潜伏中的穆连成,是天津著名的企业家,父亲是民国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,老爷子走的时候,留下了富可敌国的丹青墨宝,那也是他毕生的心血。
抗战胜利了,兄弟几个有的去了香港,有的远渡重洋去了美国,唯独我,守着这一屋子的画卷,留在了津门迎接光复。
盼中央、望中央,中央来了更遭殃。
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的机要室主任余则成,三天两头的往我家里跑,让我作为大收藏家的后人,多为戡乱救国和民国的文化事业做贡献。

老爷子在世时常说,这政治目的的捐赠,就是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。
但我也知道,如今国民党打下了天下,之前没资助过革命的我们穆家,,如果不“出血”,这关是过不去的。军统可以轻松给我扣上一个反革命的汉奸帽子。
终于,在“余主任”一次又一次诚恳的拜访下,看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资本家被军统打成了汉奸,我下定了决心,向天津政府捐赠了上百件的藏品。
一方面,这是响应国家号召,是企业家报国;另一方面,我也希望能为家人换取一个时代的“护身符”。
果然如我所料,由于捐赠的文物数量巨大且质量极高,政府为我开了盛大的表彰大会,当时的市里面亲自给我颁发了奖状,盛赞我是爱国人士。那一刻,我以为这就是结局,我用身外之物,换来了家族的安宁。
可缴纳了如此多的藏品,非但没有挡住贪婪的军统,余主任的上门更频繁了,还换了个方式,表示他很喜欢字画,想从我这“借阅”几幅还没捐出去的、最著名的藏品“鉴赏鉴赏”。
看着余则成这个青年才俊的一脸赤诚,我也知道他的无奈,满腔革命理想的他一开始也没想到,真正要想我收藏字画的不仅有博物馆,还有他的顶头上司,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,吴站长一句轻飘飘的“满满两大车文物,你就没好好参观一下?” 便将其中的部分藏品定义为伪作和不宜入藏,从中抽了出来,最后以赝品的价格卖给了龙二。

捐给国家可以,被吴敬中勒索我可不愿意,但此时的形势不由人,军统天津站,对了,如今已经改名为保密局,有个行动队长叫马奎,不知道怎么查到了,我跟八路军的邓铭主任是同学,如今国共开战在即,一旦这位拙略的行动队长说我是“峨眉峰”,找谁说理去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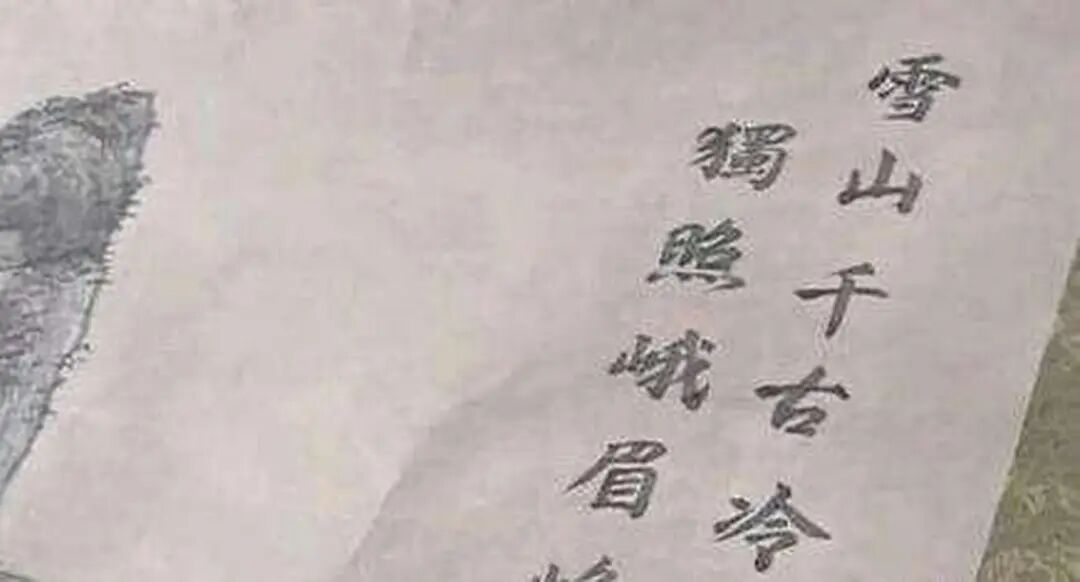
于是我再一次忍痛,将最宝贵的那几幅最宝贵的字画借给保密局的余主任“鉴赏”,希望他们能信守承诺,用完归还。
吴站长是放了我一马,但我最终还是被军统抄了家,不得已带着家人躲到了乡下,直到新中国解放后,我才得以回到故居,可家里已经四壁空空,连当年余则成们借画时留下的借条,也都在抄家中不翼而飞。
后来,我经多方打听,以为我的那些藏品都被妥善收藏在台北博物院的恒温库房里,也算是物尽其用,慰藉祖先在天之灵。
可突然有一天——我家晚秋突然发现,当年我捐出去的那些字画,竟然有一幅出现在了嘉德的拍卖会上!著名交易大师,两根金条理论创始人谢若林,说是我们是从穆氏后人手中获得,并将这件国宝摆上了货架,起拍价直逼一个小目标。
只可惜,当年从我这拿走画作的余则成已经殉国,以赝品为名购入画作的龙二也不知真人是谁,搞得个死无对证,保密局天津站也只回了一句冷冰冰的:那画当年被鉴定是假的,我们早就按几千块钱把它处理掉了,合规合法。
这一句话憋的我无语,不想当年肉包子没有打中狗,却喂饱了潜伏在暗处的狼。
哎,什么余则成我也不想骂他,他就一干活的,根本就不是主谋,剧中真正一心搞潜伏的,只有背后那个道貌岸然的吴站长。